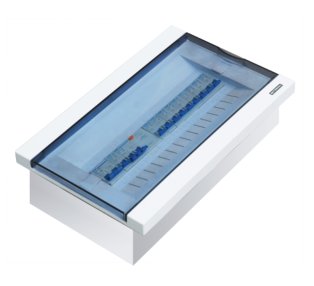正和妻子吃午饭,忽听外面房东王师傅在跟人说话,经过我的门前,往左边去了。接着是开门的声音。
又有人来租房子了。妻子说。我说,估计是的。我们隔壁这一间空了好些日子了。妻子好奇,说,我们也出去望望看,是个什么样的人。
原来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,中等个子,身材偏瘦,却很结实,面容俊秀。穿着红底黑格子春秋衫,黑色的大脚裤,平跟布鞋。头发不长,拢在脑后,马尾巴似的。脸色日晒的浅棕色。身边跟着个洋气的十来岁小女孩。
屋子很干净,女人看了很满意。小女孩说,姨,这个屋子蛮好的。女人对王师傅说,秋(就)这样定了,我下午把行李拿来。我和妻子回到屋里,妻子说,这个女的也不知是干啥的。我说,这个女的,是离婚的。妻说,你瞎嚼。你哪认得她的?我说,我哪认得?妻说,那你凭什么说人家是离婚的?我说,她还有个儿子。老家不是三仓就是新街那地方的。
妻子疑惑地看着我,像要挖出什么秘密。说,别是你相好的,故意租到我们旁边来,你们好方便?我说,你真是想象力太丰富了,等她来你问问她认不认得我。
我们这一排四户房客,合用天井里的一只水池,早晨刷牙洗脸,洗衣洗菜洗锅碗,都在一起。有时,衣服捧在手上,要等前面的人洗好,于是大家就有时间拉家常。第二天晚上我下班回来,吃晚饭时,妻子又开始审问我:你跟我说实话?你真认不得隔壁那个女的?我说,你怎么又揪住不放?那你没问她?妻说,今天一起洗衣服时我问了,她姓丁。她说她是三仓的,跟老公离婚了,有一个儿子,在市一中上高一。你说你不认得,为什么你知道得这么清楚?除非你说出个理由让我服气。
我说,其实也很简单。你看这个女的穿的衣服,就是农村妇女。脸上晒得发红,就是做农活的。她这个年纪出来租房,一定是离了婚,没有家。如果她的老公不在了,也不会出来租房。农村人离婚,像这样年纪的女人,有女儿的,一般都会跟母亲。生儿子的,大都会跟着父亲。她带来的那个小女孩喊她姨,说明不是她的女儿。她一个人出来,说明她有个儿子,跟了男方。如果她的家里没有兄弟,她会回娘家住。现在出来租房,要么他家里有兄弟,要么父母都不在世了,反正是回不去了。她看房时说了一句话,秋(就)这么定了,你还记得?这个“秋”是卷舌音,只有三仓新街一带的人这样说。所以我说她是那一带的人。这就是我的理由。
妻子怔怔地望着我说,你能上街摆摊算命了。就看了一眼,能算到这么多,你厉害。怪不得我这一辈子被你耍得团团转。我说,这不过是简单推理而已。
周日的时候,妻子说,我看隔壁小丁蛮可怜的,中午喊她来一起吃饭吧?我们几个租房的,常一起搞合作,几家把菜一凑,就是一桌,然后男人们喝酒,女人聊天,其乐融融。我说,随你啊。家里的事情你做主。
一起吃饭时,小丁说,我老公人不犯嫌,也是个好人,就是耳朵根子软。他有个姐夫做局长,姐姐在医院做医生,什么事都听姐姐的。婆婆霸道,家里什么事都要听她的,要是违了她的拗,就到丫头跟前告状,丫头就回来逼弟弟跟我离婚。我一个人,哪斗得过他一家?
我问小丁,你现在离了婚,想不想重新组建家庭?小丁说,宁可一个人过。其实我家那个人也不舍得离,被他姐姐和妈妈逼得没办法。以前外出打工,现在晓得我在城里租了房子,儿子又在城里上学,他也到城里文化大厦工地打工。我说,你们会复合的。小丁说,哪有那么容易。妻子说,你就瞎猜吧。你凭什么敢肯定?我说,凭直觉吧。
过了一些日子,我告诉小丁,这个周日中午,准备几个菜,你老公要来吃饭。小丁不敢相信,我妻子也不相信。其实,她老公干活的地方,我上班天天路过。我去找了他,做通了他的工作。
周日那天很热。当我把小丁老公领来时,小丁竟然羞红了脸。看到小丁在忙菜,汗水湿透了衣衫,小丁老公说,我出去一下,马上来。我们都不知他干啥去了。一会他回来了,右手拎着一台新电风扇,左胳肢窝夹了一盒国缘酒。他放下酒,把电扇插上电源,朝着小丁吹。原来还是个心细的暖男。小丁说,你要感谢陈大哥,把风扇朝他吹。他连忙又把风扇的头转了过来。我说,开摇头吧,大家都吹到。这时,他们的儿子也来了,进门喊道:妈。眼泪就流下来了。小丁见了,忙丢下铲子,紧紧的拥抱儿子,眼泪止不住的流。这其实是我跟小丁老公商量好的,叫儿子一起来。吃饭的时候,一家子不断给我们夫妻敬酒,感谢我们让他们一家破镜重圆。
晚上妻子好奇的问我,你怎么有把握让他们夫妻重归于好的?我说,第一,他们不是感情出轨。这就是复合的基础。第二,离婚的矛盾是婆媳关系不好,而关系不好的根源是生活在一起。小丁老公听我劝,准备在城里买一套房,一家三口的生活,从此不受外人影响。三是小丁老公只是一个打工的,人老实,重组家庭既没那个经济实力,也没有那个想法。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桥,我就是给他们搭个桥而已。或者说,需要一个台阶,我就做那个台阶。就这么简单。(陈国江)